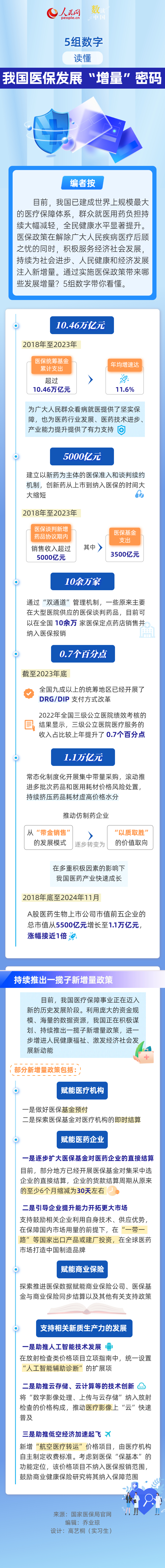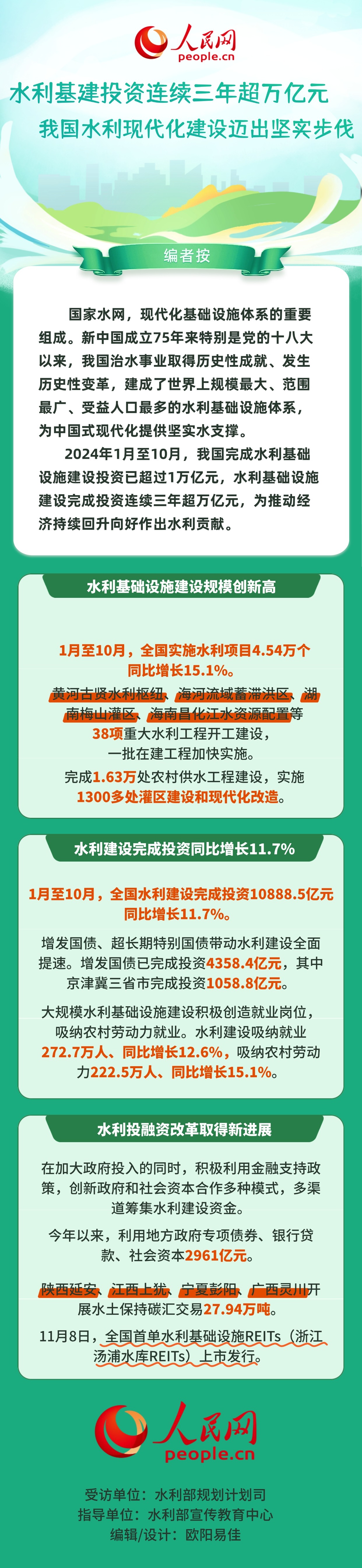图① 胡思得参加国际军控大会。

图② 胡思得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办公室工作。

图③ 胡思得在西南科技大学作报告。
北京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一栋灰色的4层小楼,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中物院”,原二机部九局、九所)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馆所在地。
11月15日,在所史馆一楼展厅,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物院原院长胡思得。
1958年,为了研制核武器,二机部在北京设立九局、九所。同年9月底,复旦大学毕业生胡思得到九所一室报到。
他告诉记者,1959年,为了给苏联承诺提供的原子弹实物教学模型提供“安家之所”,九所修建了厂房样式的模型厅。然而,直至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,模型厅未等来任何原子弹模型。
望着空荡荡的模型厅,胡思得和同事们踏上了自力更生研制“两弹一星”的征程。
“土方法”填补空白
1958年,胡思得报到时,室主任是邓稼先。
“老邓给了我们一本俄文版的《超声速流与冲击波》,让我们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多借几本。”胡思得说,但寻书无果,只能自己动手油印。
“资料印出来后,我们一人一册开始学,没有人告诉我们将来要干什么。”一个星期后,胡思得憋不住了,咨询了邓稼先。
“老邓向上级请示后,告诉我们,九所是搞原子弹的,一室负责理论研究,并强调一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”胡思得听后,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。
但摆在他们面前的,是一条难走的道路。
“模型厅盖好后,我们就开始等模型,但左等不来,右等不来。”胡思得说,后来,他知道,模型不会来了——1959年6月,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,终止了原子弹援助计划。
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。
“其实当时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,不相信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原子弹。”但对胡思得来说,更多的是兴奋和坚定,中国人终于要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。
在邓稼先的领导下,一室一直保持着互教互学的学术氛围。
“比如研究状态方程的时候,我因为比老邓多看了几篇文章,他就会让我给大家讲讲。”胡思得回忆,大家就这样你讲一段、我讲一段,把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吃透了。
胡思得领导的小组主要负责研究铀的状态方程。苏联原子弹用的裂变材料是钚,但我国那时没有钚,只有高浓铀。钚、铀的临界质量不一样,要进行原子弹理论设计,必须要掌握铀的状态方程,即高压下铀材料的密度、温度、压力和能量之间的关系。
在邓稼先的指导下,小组成员从一篇英文文献中找到了27种金属的冲击压缩数据(也称雨贡纽曲线),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数据求解材料状态方程的方法。
但27种金属中并不包括铀。铀的状态方程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,国内也尚无实验条件。
“小组群策群力,提出是否可以将27种金属的雨贡纽曲线按各种物理参数进行排列比较,找到规律,进而推出铀的雨贡纽曲线?”胡思得说,这个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可,他带领组员们分头工作。不久,组员李茂生负责的一个参数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,团队初步摸索出了铀的雨贡纽曲线。
这仅是第一步。
雨贡纽曲线的适用范围是几十万标准大气压以下。原子弹爆炸中,铀所经受的压力远超这一范围。如何将更大范围内铀的状态方程计算出来,胡思得想出了一个“土方法”。
他把整个状态方程分为了三段,对应三个范围。在低于百万标准大气压的范围内,用自己推出的雨贡纽曲线。在几亿标准大气压的极端高压范围内,“借用”托马斯—费米理论。之所以说“借用”,是因为此前这一理论被苏联专家认为只适用于天体物理研究。两个压力范围的中间部分,胡思得和同事根据上述两条方程曲线两端的走向进行外推连接,最终“凑”出了一个完整的状态方程。
回忆起当初的“土方法”,胡思得笑着说:“这实在是被逼出来的办法。”
对这个摸索出来的结果,谁也没把握。
“这个时候,程开甲先生来到九所,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。”胡思得说,后来,他和团队看到一篇苏联学者发表的论文,发现其处理大范围状态方程的方式与他们大同小异。这也再次验证了胡思得等人方法的正确性。
后来,随着理论研究力量不断加强,相关理论研究水平也不断提升,有力支撑起原子弹的设计、生产、试验过程。
助力氢弹小型化研究
1962年下半年,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已基本成型,九所的工作重心转入试验、生产阶段。从事理论设计的一室也开始着重关注理论与实际结合,为此专门成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小组,胡思得任组长。小组的任务是将理论设计方案带到青海221基地,与实验部门紧密合作,根据试验结果指导实际生产。
周光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。出发前,他特意约胡思得谈话。
“他对我说,搞科学工作,最重要的就是不放过理论或试验中存在的任何疑点。当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的时候,最可能有新的突破。”胡思得一直将周光召的这番话记在心里。
原子弹零部件对精密度的要求极高,导致成品率不高。这不仅拖慢了生产进度,也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。院领导找到理论联系实际小组,提出能否在保证试验成功的前提下,放宽公差要求?小组在深入生产一线调研后,提出了一个想法:对加工难度较大的零部件,适当放宽标准,然后通过提高容易加工部件的标准来补偿这种损失。
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是否可行,胡思得和同事们深入加工车间和试验现场,亲自动手测量、计算,反复调试,拿出了一套调整办法,证明了这一想法的可行性。“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,算是初步明白了理论应该如何联系实际。”胡思得说。
胡思得和同事们的工作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生产研制进程,并且为后来指导第一代核武器工程设计、生产、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964年10月16日晚,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,身在青海221基地的胡思得加入了游行欢庆的队伍,喜悦填满心间。
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,胡思得和小组成员返回北京,被安排参与氢弹小型化研制工作。
氢弹小型化工作,关键点在于小。要变小,结构上必须要有重大改进,而结构的改变又会对装置性能等各方面产生影响。
由于此前几个核武器型号的研发工作都很成功,大家此时有些“轻敌”,忽视了可能存在的挑战,使得这项工作从理论到试验都出现了严重问题,导致了“三炮不出中子”事故。
“我们做了三次点火出中子的冷试验,结果都不理想。”胡思得后来反思,“当初大家有些得意忘形,步子迈得太大。做核武器研究其实就像在悬崖边行走,成功的道路只有窄窄一条,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”
为了打响这一“炮”,随后半年多时间里,在邓稼先、于敏的带领下,胡思得和同事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,与试验人员紧密配合,共同设计试验方案,改进理论设计。
“我们齐心协力,一处处改进,冷试验前后做了七十多次。对从结构设计到加工生产中的各个环节,我们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。”胡思得说,为了克服特殊构型对装置性能的影响,他和同事们凭借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得来的经验,巧妙地对一些零部件作用时间进行了相应调整,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。
“最后一次冷试验时,我们圆满解决了此前的问题,打响了这一‘炮’。”胡思得说,在这次工作中,于敏等人实事求是、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他也更懂得理论联系实际,以及从理论和试验的不一致中寻求突破的重要意义。
重心转向核军控研究
自参加工作以来,胡思得亲历了我国核武器事业从无到有的“高光”时刻,也见证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核大国发展核武器事业的历程。
20世纪80年代中期,美苏等国已基本完成核武器研制所需的核试验工作,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声音愈加强烈。彼时,我国新一代核武器正处于爬坡跨越的关键时期,一旦被迫禁试,将给我国国防事业带来重大损失。
怀揣着对国防事业高度的责任心,已经病重的时任中物院院长邓稼先联合于敏启动了一项重要工作,向中央递交一份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书。
为了写好这份建议书,邓稼先和于敏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,对核大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以及国际上的禁核试风潮进行详细分析。时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的胡思得也是调研小组的一员,他几次奔走于邓稼先的病床前,全程参与了建议书起草工作。
“老邓当时刚刚做完手术,切掉了部分直肠,身子坐不下,只能窝在一个汽车轮胎的内胎上,逐字逐句修改建议书,一边改一边疼得直流冷汗。”回想起邓稼先,胡思得满是敬佩和心疼。
最终,经过细致研究、反复修改,这份言辞恳切、深思远虑的建议书日趋完善。
建议书递交后,中央高度重视,我国核武器发展也按下了“加速键”。1994年,胡思得被任命为中物院院长,主要工作继续围绕建议书展开,组织领导了我国此后的历次核试验。
1996年7月29日,是计划外增加的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日子,这一天恰逢邓稼先去世十周年。在当日举行的动员大会上,胡思得回想起一路走来的历程,感慨万分,动情地对大家说:“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,我们一定会成功!”
试验当天,一声巨响如约而至,试验圆满成功,这是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。同日,我国政府郑重宣布,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。
暂停核试验后,我国核武器事业该如何发展?这一问题,早在最后几次核试验期间,胡思得等人便已有所考虑。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,胡思得等人率先开启了中国最早的核军备控制研究。1989年,科学与国家安全研究项目(PSNSS)在中物院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,胡思得任研究组第一任组长。PSNSS成为我国对外开展核军控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。
1999年,从院长岗位退下来后,胡思得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核军控研究上。2003年,中物院战略研究中心成立,胡思得任首任主任。
如今,已经88岁的胡思得仍然关心核军控研究。没有特殊情况,他每天会去办公室工作半天,有时还要与年轻人开会讨论。年轻时多才多艺、身姿矫健的他如今饱受膝盖退行性病变的困扰,走起路来离不开拐杖,有时还需人搀扶。他还戴上了助听器。“好在眼睛还不错,看书还不用放大镜。”胡思得总是这样乐观。
当记者问起,他如何定位自己在我国核武器事业中的角色时,他笑着摆了摆手说:“我只是大海中的一颗小水滴而已。借助集体的力量,我们可以波涛滚滚;如果离开了集体,很快就蒸发掉了。”(记者 都 芃 陈 瑜 吴叶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