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刘文飞在书房。
受访者供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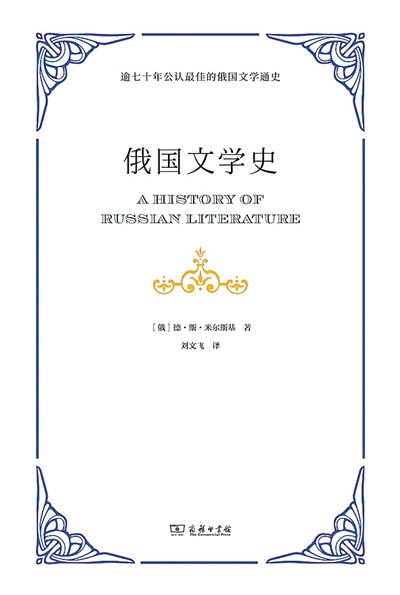

“刘文飞”这个名字与俄罗斯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无论是《萨宁》《复活》《文学与革命》等译作,还是《布罗茨基传》《苏联文学史》《阅读普希金》等专著,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40多年来,刘文飞用百余部作品为中国读者走近俄罗斯文化提供助益。集学者、翻译家、作家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他,也有一个特别的书房。近日,我们走进刘文飞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家中,听他聊治学、教学与创作中的难忘时刻,聊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心得体会。
开放的书房,多元的写作
来到刘文飞家,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他的开放式书房。与多数人不同,客厅就是他的书房。这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通向大门、餐厅、开放式厨房和卧室,满满一面墙的书架正对沙发,角落里、地板上也堆叠着各类中外文图书。书架隔层的一个角落“站”着一只憨态可掬的木雕狗熊,这是俄罗斯特色工艺品;环视墙面,还可见一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的合影,彰显出书房主人与俄罗斯的深厚缘分。
“我想刚开始做学问的人,恐怕都没有自己的书房。”刘文飞笑着说。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,他曾和许多满怀学术理想的年轻人一样,挤在集体宿舍里,用微薄的积蓄搭建起自己的图书王国。这样的集体宿舍滋养了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文学研究者,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。
“我读研时买了一个竹书架放最常用的书,比如《俄汉字典》,不常用的就装在纸箱里,摞起来塞在床底下。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现在。在刘文飞看来,学者与藏书家不同,“我们的书不是用来收藏的,而是拿来用的,经常在上面写写画画”。他认为,一本书最好的归宿是最需要它的人,刘文飞将自己的很多书,比如与普希金有关的俄文书都送给了学生。
刘文飞还谈到自己的朋友、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·尼科尔森的一件趣事。尼科尔森不久前去世了,去世之前,他在邮件中告诉刘文飞,想把自己的书捐给牛津大学图书馆,但他们说并不需要这些书。尼科尔森发现,图书馆的防盗装置只监督往外带的书,却不管往里拿的,于是他每次到图书馆就带一两本自己的书进去,留在里面。“这也代表了很多学者和爱书人对书籍的态度。”
写作、翻译、做学问,对刘文飞来说不一定非要“营造一个空间,喝着茶”才能做。他喜欢通透的环境,有时把阳台门打开,感受空气的流通。在他家里,书卷气和烟火气并不矛盾,他不会觉得家居空间与读书空间的重叠会影响自己。
这种开放的态度,也反映在他的写作中。近年来,刘文飞跨越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界限,用学术散文的特殊文体,将自己的研究和翻译成果,连同一些不适合写进论文的心得感触一道传达给读者。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》是篇剧本形式的散文,刘文飞整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、小说、回忆录,使用拼接手法,为读者还原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“写这篇文章像写剧本,但整体像散文。”刘文飞说。《茨维塔耶娃和她的诗歌》一文,讲述了俄国白银时代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生平以及她鲜明的性格、独特的诗歌语言和巨大的文学成就。文章包含严谨翔实的学术分析,字里行间亦有诗意的表达、犀利的观点和浓烈的情感,让学术得以插上一双文学的“翅膀”。《纳博科夫与蝴蝶》循着蝴蝶的踪迹,追随世界文豪纳博科夫的生命和创作历程,生动的画面感带来小说般的阅读体验。除了散文的自由表达,这篇文章还兼收各类文学体裁优势,作者希望借此拓宽散文表现的空间。如今,这类作品已收入散文集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》中,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传达俄罗斯文学魅力
刘文飞书房里最多的是有关俄罗斯文学、历史、艺术的图书。“我把自己的文字工作分为三部分,一是学术,我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《俄国文学通史》,这套书一共六卷,除担任主编外,我还承担了第二卷、第五卷的编写任务;二是翻译,主要是俄罗斯文学;三是写作,我希望写一些学术散文,把俄罗斯作家的故事用生动的语言讲述给中国读者。”
在刘文飞看来,俄罗斯文学不仅对世界文坛贡献巨大,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正如鲁迅所说“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”,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对五四新文学确立“为人生”的文学理念、开辟“血与泪”题材的创作方向有直接影响。从1903年普希金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,一代代中国作家和读者阅读着俄罗斯文学成长,《海燕》《牛虻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,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等文学理论曾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界。
接过前辈的接力棒,刘文飞写下《苏联文学史》《俄苏文学简史》《阅读普希金》《诗歌漂流瓶》《布罗茨基传》《伊阿诺斯,或双头鹰》等专著,翻译了普希金所有的抒情诗作以及《茨维塔耶娃诗选》《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》《悲伤与理智》《俄罗斯文化史》《文学与革命》等作品,总数超百部,单篇文章更是多得连自己也数不清。他为中俄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,也得到了认可。
2015年11月,克里姆林宫,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刘文飞颁发“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”。“文学更能体现友谊,”刘文飞在颁奖现场说,“我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,为中俄之间的文学友谊继续努力,因为文艺最能加强中俄友谊。”领奖后的这些年,他毫不懈怠,如今,刘文飞又忙着校对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茨基的《俄国思想史》译稿,准备交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
在刘文飞看来,缺乏思想史的梳理,可能会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过于狭窄。这也是他翻译《俄国思想史》的原因。“最好是两者进行对读,从文学史和思想史两个角度观察俄罗斯文学,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下看俄罗斯文学,又从俄罗斯文学中析出其思想史意义。”
俄罗斯文学浩如烟海,选哪本文学史作为指南呢?刘文飞推荐了米尔斯基的《俄国文学史》。这本书入选2020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“十大好书”,在豆瓣深受读者好评,位列外国文学史图书榜单第九名,评分高达9.6分。“米尔斯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和苏联文学界、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,他的生活经历和文学活动堪称传奇,也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和象征。”刘文飞说。他发现,欧美大学的斯拉夫语系都用这本书作为教材,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,一定会对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中国读者产生巨大帮助。
《俄国文学史》从古代俄国文学(11—17世纪)讲起,经古典主义时期、现实主义时代、美学新思潮、象征派兴起,至1921年小说复兴结束,话语风格极富个性、独树一帜,被纳博科夫称为“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”,牛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·史密斯也认为,“这部著作始终在英语世界保持其地位,逾70年不变,这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记录”。
对于俄罗斯文学研究与翻译,刘文飞信心满满,他认为:“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准,与我们的欧美同行、日韩同行相比毫不逊色。去俄罗斯出差时,总会有俄罗斯同行问我,是否已经翻译过他们某某作家的作品。我和他们开玩笑说,这种问题以后不必再问了,中国译者早就把你们国家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全翻译了。”
做好中外文学的“摆渡人”
“我最大的遗憾是只会两门外语。”刘文飞说。他建议,年轻人如果有机会,要多学几门外语,除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外,有能力还可以学学拉丁语、希腊语。在他看来,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尽管文学翻译能为读者打开世界文学的大门,但还是有局限性,无法做到“无损”地传递外国文学经典的魅力。“语言和文学是统一的,不懂某种语言,某种程度上就无法完全读懂这种语言的文学。但我们做翻译的人,还是要做好中外文学的‘摆渡人’,让广大中国读者通过阅读外国文学经典,开阔国际视野。”刘文飞说。
2022年,刘文飞与几位翻译家一起,与《十月》杂志合作,商讨开一个新栏目——“全球首发”。今年以来,该栏目邀请一系列世界知名作家,以中文形式全球独家首发重磅新作。截至目前,该栏目已刊发5期,发表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、俄罗斯作家沃多拉兹金、南非作家库切、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、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的新作。
“我联系了俄罗斯的当红作家沃多拉兹金,通过首发他的新作,《十月》的读者能第一时间、无时差地了解世界文学风向。这一栏目,也让《十月》从一本中国文学期刊,变成一份国际文学期刊。”刘文飞说。
多年来,刘文飞的世界文学推广工作从校内拓展到社会,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开设通识课“外国文学名著导读”,每年选课学生达数百人;他在全国高校、图书馆等举办讲座百余场,拉近中国读者与世界文学的距离;作为评委,他参加多项评选评奖,如鲁迅文学奖、上海译文社的双年奖等,推介优秀译作;作为编者,他策划多套大型丛书,如《普希金全集》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》《普里什文文集》《巴别尔全集》《双语对照外国诗丛》《当代俄罗斯长篇小说丛书》等。
“在首师大开设‘外国文学名著导读’通识课给了我重新阅读世界文学经典的机会,我将授课成果写成文章,发表在《边疆文学》《十月》开设的‘读与被读’栏目中,后来结集出版为《读与被读》单行本。”刘文飞说。
《读与被读》是作者打破文化隔阂、拥抱世界文学的产物。这本书从西方文学源头《荷马史诗》讲起,从文学伦理、宗教感、“双重人”形象、“笑文学”、死亡主题等方面突破,巧妙解读荷马、但丁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、歌德、雨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乔伊斯、川端康成、纳博科夫11位世界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。
“我觉得各国文学,包括东方文学,都是大同小异。大同小异不是指风格写法,而是指精神内核。就像我在解读《荷马史诗》的“悲悯”时所说,你会发现每一个作家都是人道主义者,每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教人向善。就像布罗茨基所说,文学是伦理学之母。”在他看来,阅读世界文学经典的最大好处是能开阔我们的胸襟,让我们通过文学向善。“文学用美的形式唤起我们心底的善。这是世界各国文学,尤其是经典作品的共性。”

